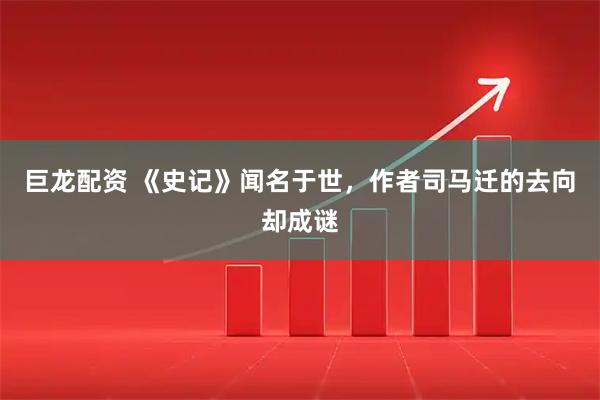
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,这是后人对《史记》的高度赞誉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,《史记》流传千古,成为了历史的瑰宝,而它的流传,也反映了它不朽的价值。司马迁,凭借这部伟大的作品成就了自己,也让后世铭记了他的名字。然而,奇怪的是,在《史记》完成之后,司马迁仿佛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去向成谜,令人不禁好奇:这个为后世留下如此伟大作品的历史巨匠,究竟经历了什么,最终去了哪里呢? 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司马迁去向的记录。而同样身为史官的东汉班固,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,也对司马迁的结局含糊其辞,仅用迁既死后,其书稍出一笔带过。这种处理方式,无疑令人生疑。班固作为司马迁的后继者,他显然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事情,但却没有详细说明。或许,他有自己的原因,想让司马迁的身后多留些清静。 公元前99年,李陵随汉武帝的外戚李广利征讨匈奴,李广利的主力并未遭遇匈奴主力,而李陵却与匈奴单于的军队在浚稽山相遇。李陵带领五千汉军步卒,与匈奴精锐骑兵激战七日。单于不断调兵包围,李陵因箭矢尽、兵力悬殊,最终选择投降匈奴。这一战,汉军虽杀敌万余,却未能避免惨败。汉武帝不仅因李陵投降而愤怒,还因李广利无功而返,失去了颜面。满朝重臣纷纷站在汉武帝一边,批评李陵,唯有司马迁提出客观分析,认为李陵的投降是无奈之举,且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足以抵消投降的过错。此言触怒了汉武帝,最终,司马迁因言辞得罪了权力,遭受宫刑。从那一刻起,司马迁的内心已经死去。 在封建社会,史官虽地位卑微,但却肩负着编撰史书、记录历史的重任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曾提到: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,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,主上所戏弄,倡优畜之,流俗所轻也。假令仆伏法受诛,若九牛亡一毛,与蝼蚁何异?他将自己与卜祝巫师相提并论,认为史官不过是帝王身边的工具,连自己的生命也如同蚂蚁一般微不足道。可以说,司马迁的隐忍和屈辱,不仅来自于他个人的遭遇,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官的悲惨处境。然而,他依旧选择坚守自己的使命,忍辱负重,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历史理想,更是为了父亲的遗愿。司马迁的父亲,司马谈,在临终时曾叮嘱他:予死,尔必为太史,为太史,勿忘吾所欲论著矣。父亲的遗愿成为了司马迁心中的责任,完成这部史书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,更是为了向父母尽孝。 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;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也。这是父亲司马谈给司马迁的教诲。父亲告诉他,孝道的最终意义,是通过自己的成就,让父母的名声在后世得到彰显。司马迁将完成《史记》视为自己人生的头等大事,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,因为他深知,只有将史书写成,才能为父亲实现遗愿,也为自己赢得历史的尊严。他曾以先贤为榜样,激励自己: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成。 这些话语看似充满自勉,但对于司马迁而言,他心中的痛苦与屈辱,远比这些先贤所经历的更为深刻。周文王被囚禁、孔子受困、屈原流放、左丘明失明、孙膑遭受残害、吕不韦迁蜀、韩非被囚,他们的遭遇虽然也充满坎坷,但与司马迁的宫刑相比,仍显得相对轻松。宫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是无法言喻的耻辱。普通百姓遭遇阉割,可能是生活的无奈选择;但士大夫阶层,宁死也不愿接受与阉人同列的屈辱。身心的伤害远比外在的肉体痛苦更为深重。 即便如此,司马迁依然坚持完成了《史记》,然而,随着这部伟大之作的诞生,司马迁的精神也逐渐崩塌。目标达成后,他的内心再也没有当初的激情和执着,只剩下无尽的空虚和绝望。年轻时的游历梦想、山水情怀,似乎在这沉重的历史任务面前都成了奢望。修史的理想虽然没变,但心中的伤痛已经无法愈合。 《史记》成就了司马迁,但也让他从此陷入了人生的低谷。他曾经的理想和热情,在历史的重压下逐渐消磨殆尽,最终,在创作完成后,他或许会选择自杀,来彻底洗净身上那份深深的耻辱。毕竟,在那个时代,士人的风骨与尊严比生命还重要。而如果说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,那么他也很有可能会选择隐退,远离宫廷的纷争,去寻求心灵的宁静。毕竟,年轻时他曾醉心于山水人文,游历四方,纵情于自然与文化之中。如今,已经看透了权力的肮脏与官场的腐化,或许他会再次踏上那条寻求内心平静的道路。 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并未详细描述司马迁的去向,这或许正是为了给这位历史巨匠留下更多的清静和尊重。究竟司马迁的最后结局如何,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在历史的洪流中,许多事是身不由己的,人生的悲欢离合,往往无法按个人的意愿左右。
发布于:天津市恒汇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